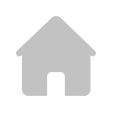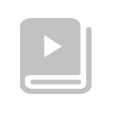[关键字] 常识产权;私权;常识共享
1、常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常识产权规范从其产生到目前,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但历经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不同时期,其进步过程就是一个科技革新和法律完备相互用途、相互促进的过程。常识产权规范随着着工业文明而生,它不只适应着科技和经济进步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设定的法律机制推进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
常识产权作为一种勉励机制在于明确赋予常识革新者以某种特权,让其对我们的成就在肯定的期限内享有独占权。依赖这种独占权,可以获得革新带来的超额收益,在激起革新者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达成了社会的利益,促进了经济的兴盛。这是对常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最基本的原因。同时,大家也看到,对常识革新者进行保护,还基于客观的实质状况。一方面,革新者在革新的过程中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本钱,并承担商品上市后的风险;其次,常识特有些共享性决定了它可以随便地被复制和传播,其自己存活能力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的干涉和保护,预防和制止其他人非法占有些任务就势必由政府承担。政府的本钱在保护得力的状况下,可以由相应常识产权产生的税收收入弥补。假如政府对常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则会紧急挫伤革新者的积极性,也会导致资源和人才的流失。
对常识产权私权属性的一定,为权利人提供了最经济有效而持久的革新动力,保证了科技革新活动的不断进步,促进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对常识产权买卖规范的确立,则促进了常识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借助,达到常识技术功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和惩处,既是对产权所有人的利益保护,也是对市场角逐的规范管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常识产权的《与贸易有关的常识产权协议》作为大家需要遵守的协议,也需要大家尽快健全大家的常识产权规范,做好常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2、常识产权保护势必引发利益冲突
大家在保护常识产权的同时,需要认识到,常识产权的权利设定能给予权利人相应的物质勉励,但常识产权并不势必保护权利人借助权利无限地获得收益。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并不是是常识产权规范的终极目的,鼓励促进技术革新和维护公共利益才是常识产权规范的基本宗旨。TRIPs第7条规定:常识产权的保护和权利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的改革、技术的出售与技术的传播,以有益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法去促进技术常识的生产者与用户互利,并促进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伴随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常识产权法律规范及其实践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常识产权范围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Microsoft的价格歧视和捆绑销售案件、南非公共健康危机事件等都凸现出常识产权保护和禁止滥用中平衡协调利益冲突的必要性,其中主要体现为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冲突。
常识产权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是私权,保护常识产权权利人的个体利益是常识产权规范的中心内容。但对常识产权进行限制以满足社会公众利益也有着迫切的需要和法理的正当性,在公共健康问题下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冲突看上去愈加突出和现实。怎么样妥善协调常识产权中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成为常识产权保护中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作为一个客观范畴,利益是大家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法和手段。“利益决定着法的进步和运作;法律影响着利益的达成程度和进步方向。”①“法学家所需要干的就是认识如此一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如此一种形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保持这类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②
常识产权人个体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常识产权规范保护个人利益有着坚实的现实依据和法律逻辑。常识产权规范促进科技的进步,是通过保护和鼓励常识产权人的创造创造进行的;其法律权利的设定也是针对特定主体的,完全符合法治精神并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常识产权权利人法定权利的确定是对社会公众的一种义务需要和权利限制。但对独占权的保护过度,会妨碍常识的传播和应用,限制公众对技术的用法,而且享有独占垄断权的产权人没角逐重压,不会努力地进行技术开发,最后不利于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进步。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过多强调权利人的权利而致使权利人滥用权利的纠纷屡有发生。
现代社会权利义务体系需要大家在倡导权利和行使我们的权利时,注意“度”的限制和约束,顾及别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在协调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时,应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适合的平衡,使赋予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
3、常识产权保护与常识共享的冲突
《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在宣布每个人都有权保护其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与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参与社会文化常识,以享受艺术和推荐科学的进步与利益。”可见,保护自己创造的常识产权与推荐社会文明的成就均属基本人权,两者不可偏废。
对常识产权保护和常识共享冲突的不同抉择会衍生出不一样的状况。前苏联和少数进步中国家的立法过去出于进步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需要,限制常识产权创造者的利益,甚至规定绝对限制私权的规范,这种做法完全剥夺了常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挫伤了科技研究者的积极性。与之相对,绝对地将常识产权视为个人的财富而排斥社会利益,或不加剖析地允许常识产权人完全自由的行使其权利,都可能有损于社会公益。对于后者,大家可以从药品常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健康危机问题来看,尤其是国际社会发生的与公共健康有关的重大常识产权事件引发了激烈讨论。
全球公共健康危机所导致的影响超出了大家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关心,引发了全球关于常识产权保护合理性的讨论,常识和技术是应当由私人企业为其个体利益所垄断,还是应当促进社会进步,用于帮助降低贫困、饥饿和疾病,这是讨论的中心问题。考察常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大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常识产权不是绝对的财产权,在具备私权性质的同时,还具备公有性和共享性。从常识产权的产生来看,常识产权就具备个人创造性和社会性的特征。一方面,常识产权商品中深刻体现了创造者的个人风格,是个人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其次,常识产权又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产物,任何一个常识商品都是在继承前人出色成就的基础上加以扬弃的结果。因此,仅将常识产权视为个体的绝对性财产并不确切。从常识产权的最后归属来看,绝大部分常识产权的商品最后都进入了人类社会,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所以,假如将常识商品绝对视为个人财富而拒绝排斥社会公益,不只歪曲了常识产权保护的最后目的,并且也很大地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
[1][2]下一页